野调荒腔说冥簿(上)
记得小时候看《西游记》,曾有一大遗憾,那倒不是因为孙悟空没有坐上灵霄宝殿,而是他大闹森罗宝殿,勾抹生死簿时,心里只想到猴子中有名的大人物,“九幽十类尽除名”,而我们人类却不在其垂顾之内。原来这猴头也不过是个自了汉!于是想到将来难免森罗殿一行,便不免对他那场上天入地的造反行动少了些佩服。
如此很是耿耿了几年,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,领教了人间造生死簿的手段后才释然于怀。从此明白了“人身后未必是鬼,鬼后面则肯定有人”,所谓生死簿,原来还是操在人的手里。那么还有必要再谈冥府中的生死簿吗?必要当然谈不上,但说说也无大妨碍,因为由此多少可以了解一些过去的那个时代。只是说得无板无眼,且跑调串词,与“正宫端正好”是不搭界了,自我抬举一下,也不过就是“野调荒腔”吧。
一
严格说来,“生死簿”只是冥簿的一种。冥府簿籍,除了仅注寿夭大限者之外,与“人事”(我们人类也只管“自了”,披毛戴甲的就随它去罢)有关的簿籍还有很多种,仅说重要的,就有备案食料、利禄、功名的,有随时记录善恶、功过的,还有勾捕生魂的名册,登录死鬼的户籍,而名称也是簿、册、录、籍,不一而足。但归根结底,这些东西的要点总不离生灵死魂的“生死”二字,所以看到《十王图》中判官手中所持册子,不管他正在翻检着什么,即便一概称为“生死簿”,也不能算是大错。
中华文明中引以为豪的东西实在不少,官府簿籍制度创立的早与完备就是其中之一。刘邦入关中,克咸阳,诸将争取金宝,萧何“独先入收秦丞相、御史律令图书藏之”,于是而尽知天下厄塞、户口多少强弱。后世有人叹息:秦始皇帝焚诗书百家语,但并未绝灭,博士所掌自有副本,萧何为什么不赶紧抢救出来呢?结果西楚霸王又来了咸阳一炬,弄得典籍灭绝,从此给儒生找了事,有的收拾断简残编寻找超高指示,有的趁机造假弄鬼给新贵喝道,有的考证求真让人下不来台。其实这些儒生也是瞎忙,岂不知掌握了天下户口厄塞便有了打天下的重要资本,“刘项从来不读书”,及至坐了江山,孔老二不是也要听刘老三的吗!书呆子不识大体,往往类此,所以他们只配摘下帽子替大英雄接尿。
与此同理,冥府要想统治和管理生人死鬼,也非有簿籍不可。由孙行者那一场大闹的结果可以看出,冥府如果没有了猴子的生死簿,也就等于失去了对猴子的统治权。冥簿就是冥府的灵魂,所谓冥官,只不过是用冥法管理冥簿的鬼员而已。而这冥簿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记录生人平日“善恶”的案卷,人间世中,无论是人事部门的档案袋,特务机关的黑材料,准备时机成熟再结算的明细账,还有一些人世衙门里尚缺,但已经在道德家肚子里憋馊了的整人坏主意,都为这种善恶簿提供了样板。按照我们本土的传统,“天道福善祸淫”,人的寿命长短,家族的兴衰,就要靠这善恶簿的统计结果决定。而另一种大约是西方传来的说法,人的寿命长短是前世留下的业报,并不受本世为善为恶的影响,但此生的善恶就是来世果报的依据,善恶簿就越发不能少了。
所以,冥簿虽然种类繁多,但从“结算”的角度来看,却只分两大派,无以名之,姑称之为时、空二派。
“空间”派,每人的寿命就像一间空房子,等他在人世犯下的罪过把房子填满,所谓“恶贯满盈”,他也就该死了。但也不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,人的寿命好像是一捆筹码,每犯一件过失,就根据其大小而抽掉一些,这叫“减算”,等到归零,也就算玩完了。可是如果你做了善事呢,那就要“增算”,给你添加寿命的筹码。这似乎很公平,但也不然,有人干的缺德事已经罄竹难书了,但还活得很自在,有的人刚生下,只不过哭了几声,顶多是用声音污染一下环境吧,就突然寿终正寢了。这事真不大容易说清,要想强做解释,大约只能说每个人的“房子”大小不一,筹码有多有少吧。但不管怎么看,按照这一派的观点,人的寿命长短起码可以由自己决定一部分,那就是多行善举,少做缺德事。
“时间”派,每人的寿命长短是天定而不能改动的。某公在人世犯下的罪过,冥司只管记入簿子,账要待秋后才算。也就是说,哪怕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,秦桧那样残害忠良,他们照样活得很滋润,直到天定的“大限”到了,那时再到阎罗王那里算总账,而所有的果报则或在地狱里,或在下一世,总之是不会让你们看到的。同理,这辈子做了多少好事,也是白搭,因为此生的祸福寿夭已经排定,你只能把积分用到来世消费了。过去城隍庙的大梁上悬着一个丈数来长的大算盘,有的上面还写着四个大字“你也来了”,让人不觉悚然。这个“你”本是死后的魂灵,但其实却是给活人看的,意思是你英雄一世,称霸于一国或一条胡同,终究难逃一死,总有算账的时候。但大英雄看了不过一笑,死后算账与否哪有准头,眼下我就能把你这城隍窝拆了!
总之,一个好像打排球,输够分就下台;一个好像打篮球,以时间为度,可以尽着兴地输。这两派当然也可以考查出一些中外或道释之分的痕迹,也能看出其间凿枘不能相入之处,但却从来没有发生过争执,而且还能交相作用,互为弥补,红脸白脸配合得很不错。一会儿是教育草民们只须多多行善,终将善有善报;一会儿是辩解权贵豪绅们虽然累累为恶,却不必恶有恶报。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皆大欢喜,无不和谐。所以这两派貌似相反,其实是个双面人,千百年就这样摇晃着脑袋走了过来。
二
中国最早的冥簿似是空间一派。
大约产生于东汉的“土府”,可能是中国最早相对独立于天庭的正式冥府了,它就是以“善恶簿”起家的。早期道教经典《太平经》,其《庚部之八》言天帝对生民的控制,通过“善恶之籍”记录生民平时的言行,一旦恶贯满盈,就把他们的灵魂交与“鬼门”中的“地神”,由地神审问、用刑,然后交与“命曹”核对其寿命与恶迹。如果其恶行已将寿命折尽,此人就该“入土”了,而且其罪孽还要影响到他的家族后代,这正是儒家“积善之家必有余庆,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”的诠解。
但按儒学的经典所说,如果不是特大之罪,好像并不影响子孙。所谓“大罪有五,杀人为下”(《大戴礼记·本命篇》),除了逆天逆伦要罪及后世之外,杀人也不过是“罪止其身”,绝无株连的。粗看起来,古代的统治者还是很厚道的。但一细想却更是可怕,所谓逆天地、诬文武、逆人伦、诬鬼神,这不就是思想罪吗!思想罪要罪及二世至五世不等,上掘祖坟,下诛子孙,相比之下,杀人放火反倒成了仅“上过失一等”的轻罪。这才让我明白,历史上的那些文字狱的株连范围为什么那么漫无边际,而那场纵连五代、横扫九族的浩劫冠以“文化”二字实在是再切实不过了。
至《庚部之十》,则除了提到土府之外,还有其他一些阴官,每至年终,要汇编天下生民的“拘校簿”。“拘”是拘捕,“校”是考问,拘校簿就是记录生民善恶以备拘讯的册簿。此时山海陆地从祀诸神都要把材料汇报上来,各家的家神平时监督着生民的言行,每月都要汇总,此时自然也要呈报如仪。然后就由“太阴法曹”来进行统计核算,再召“地阴神”和“土府”,由他们负责拘捕和审讯。这一套官府程序听起来很吓人,但对早就习惯了敲剥的百姓来说,也不过应了“大不了是个死”那句话而已。
但想不到的是,区区草民也要有那么多山海诸神和家神一起伺候着,给自己做着“起居注”,这倒是有些劳驾不起。所以后来就把这特务机构精简了,专职从事此业的就是道士们关心的“三尸”。(而一般草民则更愿意让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灶王爷来兼充此职,那大约是因为灶王爷颇通人性,易为小民收买,对老天爷并不很靠得住的缘故吧。)三尸神潜伏在人身体内,每过六十天,到庚申之日就要偷偷溜出去向特务头子汇报。按说修道之人以行善为本,原不必担心这汇报的,但三尸神为了想早日脱离人身的束缚,混个纱帽戴戴,便乐于让此人早死,所以一定要编派些莫须有的东西。而修道者也有他的主意,每逢庚申之日便熬着不睡,让三尸无机会溜出,日积月累,最后熬得“三尸神暴跳”(从小说中借用一下,却不是与“七窍内生烟”配对的那意思),终于气死,这位老道便不成仙也要成精了。
由此可以看出,空间派的冥簿原来与中国本土的道教有此渊源,所以载于《太平经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。用阴柔的办法对付密探,堪称黄老之术的精髓,未始不可为后人法;可是那善恶之簿却正顺遂了后世正人君子的愿望,补了“阳间官府无记人功过之条”的缺憾,对老百姓来说,又不是“大不了是个死”就能支应过去的了。
到了汉魏之际,西方的佛教僧侣已经断断续续来了几批,虽然尚不能自由自在地到民间传教,但佛教的经典却已经开译,其中的幽冥之说中就有了一个大铁围山下的八热八寒等地狱。但他们翻译时一不留神造了个“太山地狱”的词。太山,本有极大之山的意思,说的正是大铁围山,但外国和尚没想到中国的东岳泰山也可以写作太山,更没想到自己的太山地狱被地头蛇拿走,改头换面之后成了人家的东西。原来此时中国本土的宗教也正在云起潮涌,五斗米道的张鲁甚至在汉中搞起政教合一,大英雄曹孟德觉得这不是什么好事,所以平定汉中之后,“魏武挥鞭”,就赶羊似的把势力范围之内的各流方士都轰到京城里,用养起来的形式关起来。散居乡野的方士进了大都市,三教九流也有了互相观摩交流的机会,而和尚在当时也不过是方士的一种,估计佛教的“太山地狱”就是在这时候被乡巴佬的方士“借鉴”成Made In China的“太山府君”了。钱钟书先生说:“经来白马,泰山更成地狱之别名。”泰山从神山化成鬼府,正是佛教传入之后的事,而此时太山府君衙门中的冥簿,便出现了时间一派。且看下面这个太山府君掌冥之后的故事:
汉献帝建安中,南阳贾偶,字文合,得病卒亡。死时,有吏将诣太山。同名男女十人,司命阅呈,谓行吏曰:“当召某郡文合来,何以召此人?可速遣之。”(新辑本干宝《搜神记》卷二一)
冥府抓错了人,弄得人死错了,不该死的死了,而该死的却还活着。回头再看看《太平经》中的抓捕程序,可知这种抓错的事,在以善恶簿为依据时就不大容易发生。但现在的冥簿只看大限已至者的名姓,重名的多了,再查一下籍贯,偶尔一疏忽,就把不相干的人勾将过来了。而按时间派的严格规定,此人如果死期不到,冥府也就不能收他的魂灵,像人世官府那样死不认错,将错就错,或者李代桃僵,当成替死鬼把人扣下的事,是不大行得通的。既然不能收,就只有送回,否则被误抓者就成了没户口的野鬼游魂,堕落成亡命徒,从此作祟于阴阳二界,那也是很让人头疼的事。(这问题后来出了解决的馊招儿,那就是设了一个类似收容所与集中营相混合的枉死城,另文再谈。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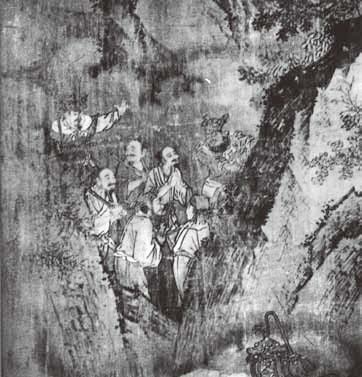
鬼卒驱赶亡魂。
——山西新绛稷益庙壁画地狱图
这位贾文合还算幸运,司命接收时才发现重名者竟有十人之多,细查之后果然有误,只有速速放回。而贾文合在归途中又遇一女郎,也是抓错放回的。但冥司混账,抓时是急急风,哪怕是弱女子,几个冥役也如狼似虎般扑上去抢镜头,而放掉时却一哄而散,谁也不管了。那女郎在昏黑的冥途中举步维艰,幸亏遇到小伙子贾文合,二人相帮着总算回到了阳世,同时又成就了一个好姻缘,让人明白好事原来都是从坏事变来的,办喜事时别忘了第一个要给抓你的阴差大哥送喜糖。
三
自汉魏以来,冥府“抓错-放回”的故事数不胜数,可以说是幽冥故事中的一大类型。虽然这一类型的要素中总少不了那本生死簿,但故事的要点并不在于证明生死簿的权威,当然也不是为了成就贾文合、杜丽娘之辈的好事。这一类型所以反复演变,被佛教徒不厌其烦地宣讲,乃在于插入了参观地狱的情节。抓错了,理应放回,但阎王爷还兼理着幽冥世界的宣传部长,于是说,总不能白来一趟吧?便让来人把九幽十八狱参观了一遍,而且不知弄了什么鬼,平时一场梦醒都要忘得七零八落,此人死而复生却能写出一篇生动的地狱游记。总之,这一类型的主题是宣传冥狱和果报,为佛门招揽信士。
但以生死簿与命定说为主题的类型也有,那就是冥官持生死簿到战场上给尸首点名的故事。
这也是一个有近千年生命力的幽冥故事母题,最早见于唐人谷神子《博异志》和薛渔思《河东记》,而直到清末仍然为人津津乐道。《博异志》讲的是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平淮西吴元济时的事。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,与唐将李愬战于青陵城,项后中刀,堕马而死。至夜四更时分,他忽如梦醒,听到有军将点阅兵士姓名的声音,呼至某人,即闻大声应诺。如此大约点了千余人。赵某侧耳听之,可是直到点名完毕,也没有呼自己的名字。不久天就亮了,点名的人早已不见,赵某挣扎起身,环视左右死者,全是夜来闻呼名字者,他这才知道原来是冥官点阅,战死者也是有宿命的。
故事的主题就是“宿命”。但人既已死,冥司只须点鬼魂之名就是了,为什么还要与死尸核对呢。莫非军事化的鬼魂也要集合排队然后开步走?道理是讲不大通的,可是那夜半点名时死尸应答所造成的恐怖气氛,在鬼故事的创作上无疑是成功的。它堪与毛僵、尸变、回煞、讨替等恐怖题材并列,因此在后代就不厌其烦地重复,但也不时添些新的作料。于是而有“指姓名叫呼,尸辄起应”(南宋洪迈《夷坚志补》卷十“王宣宅借兵”条),点到名字,已经成了僵尸的死人要硬挺挺地跳起来喊“到”,然后再咕噔一声直梆梆栽倒。月色惨淡之下,千百僵尸此起彼伏地折腾,这“活死人之夜”的场面让人想起来都毛戴。可是似乎还有再发挥下去的余地,于是到了清初人写的《蜀碧》那里,竟要“每一呼,死者提头起立”了。秀才公举人老爷们屡战于考场,明白验明正身的必要,便认为冥簿中也要有“年貌”一项,似乎死者如不提着“血模糊”的髑髅便容易被当作冒牌货一般。这种纯粹追求惊悚效果的创造,就是最恐怖的“尸变”都无法与它相比了,可是蒲松龄老先生仍能把古战场之夜的恐怖气氛再推上一层。
《聊斋》中有《辽阳军》一则,也是套用点名的程式,只是命不该死的那人头颅已断,冥官便命左右把他的断脰续上,然后送他离开,算是一些新意,却并未做其他的渲染。而《野狗》一则,写清兵镇压于七之乱,杀人如麻,一人逃难经此,僵卧于丛尸中装死。及至清兵离去,已是夜深:
忽见缺头断臂之尸,起立如林。内一尸断首犹连肩上,口中作语曰:“野狗子来,奈何?”群尸参差而应曰:“奈何?”俄顷蹶然尽倒,遂无声。
忽然的尸起如林,又忽然的蹶然尽倒,于是深夜中一野死静,等待着最可怕的东西上场。此篇虽然不是“战场点名”的故事,但袭用了那故事的恐怖环境,把清兵杀戮百姓的屠场写得惨烈无比。那么如果是船沉了淹死在江河里的呢?据吴炽昌《客窗闲话·续集》卷四“富贵死生定数”条所记,也照旧要有冥吏来点名的。那自然不会有荒野僵尸的倏忽惊乍,但想象那一具具悬在水中的死鬼飘悠悠地排起队来,就别有一种阴森了吧。
但故事也不止于制造惊悚而已,宿命的主题也在深化,于是命不该终者不唯不点名,冥官还要点破此人应在若干年后死于何处。南宋周密《癸辛杂识·别集》卷上记南宋宁宗时一事:金人南侵,杀戮甚多,积骸如山,数层之下,复加搜索,击以铁锤乃去。有一人未绝,夜见有官府燃灯呵殿而来,按籍呼名,死者辄起,应已复仆。及至其人,亦随起应之。此时便听有人言云:“此人未当死。”于是按籍曰:“二十年后当于辰州伏法。”此人既得免死,尽管他此后特别小心不去辰州,安分守法,但最后还是没有躲过这宿命,在辰州法场挨了冤枉的一刀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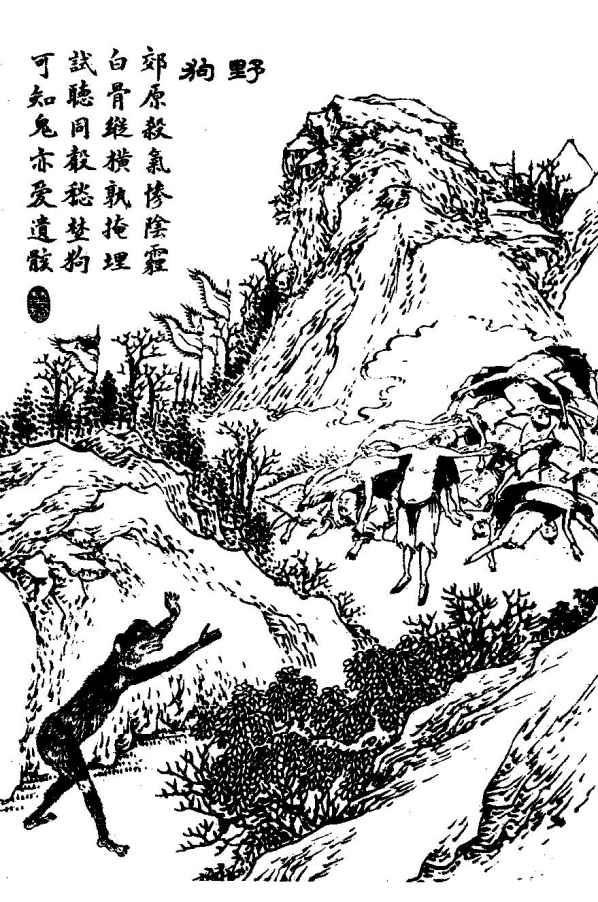
《聊斋志异·野狗》的插图,画得很失败,远不能把活死人之夜的恐怖表现出来。
此后明人陈霆《两山墨谈》卷十二“土木之败”条、董榖《碧里杂存》“婼某”条、钱希言《狯园》卷九“点鬼朱衣神”条,继续抄袭,清人薛福成《庸庵笔记》卷六“死生前定”条所记基本上也是这一套,没有什么新鲜东西。只是到了清人陈彝《伊园谈异》卷二“周大麻子”条,“空间派”才想起介入这一故事套数。
咸丰己未、庚申间,太平军占领大江以南镇江以西地区,江北扬州一带无恙。江南被陷百姓企图偷渡,多为逻骑所杀,江岸横尸如麻。某甲未死,卧于尸中,夜闻呼声自远而至,却是城隍神率冥吏持簿呼尸点名。至某甲,城隍曰:“非也,此明日周大麻子劫内人也。”次日,某甲遇一女子,自言银钱被抢,无以为生,便要寻死。某甲想,反正今天要死在周大麻子之手,留钱何用,便慷慨赠给了女子。果然一会儿就遇到一将挥刀赶来,某甲便直呼“周大麻子”,其人问:“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?”某甲凑上前说:“我今天命该死于周大麻子之手,请赶快把我杀了吧。”周大麻子诧道:“神经病!你让我杀你,我偏偏不杀。”于是某甲追着让周砍自己脑袋,周大麻子却像见了鬼似的,把抢那女子的银子一丢,策马绝尘而逃了。故事好像有些变化,其实不过是把另一种行善改变宿命的老套子穿插进来,说到底,还是不离“宿命”二字。[1]
冥簿中的宿命,追究起来是很冷酷无情的,它让屠伯的草菅人命俨然成为“替天行道”了。北宋黄休复《茅亭客话》卷六有“艾延祚”一条,就用冥簿点名的故事为镇压成都李顺起义的屠戮做辩护:“乃知圣朝讨叛伐逆,屠戮之数,奉天行诛,固无误矣。”朝廷杀人是恭行天讨,成千上万的百姓被屠戮,绝对无一冤枉。那么外族入侵时对平民百姓的屠戮又算什么呢?南宋蔡绦《铁围山丛谈》卷四谈到南宋建炎初,金兵南侵,朝廷扔下百姓继续南逃,豫章沦陷。有郎官侯懋等三人未及逃离,藏在一座园林的堂屋大梁上。一日见有金兵数十百人继来,共坐于堂,命左右把逻捕到的百姓,不论男女老少,一律用大棒子敲杀,积尸无数,直到天暮死尽始去。到了夜里,冥官又来点名了,其中只有四尸冥吏说“不是”,第二天果然只有此四人活了过来。这当然也是天命如此,与朝廷的腐败无能、只管逃命毫无关系了。饥荒、冱寒、兵燹、瘟疫、洪水、地震,这都是老天爷“收人”。既然是老天爷要收,你不去行吗,皇上想拦住行吗?何况万岁爷是真正的天之子(这时候可不要把领助学金的“天之骄子”也扯进去),帮他老爹一把岂不是天经地义?
四
由前面所引的《太平经》可知,善恶之簿可以说与冥府同时出现。其总的情况,虽然时历两千年、阎王爷换了二百代,却也没什么变化,就是特务汇报、冥吏汇总那一套而已。
这种记录功德罪过表现的簿子,到了唐代或被称作“戊申录”。何为“戊申”,从来未见有人解释过,好在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中对它的格式做了记录:“录如人间词状,首冠人生辰,次言姓名、年纪,下注生月日,别行横布六旬甲子,所有功过,日下具之,如无即书无事。”登入此簿的人“数盈亿兆”,据掌管此簿的朱衣人说:“每六十年天下人一过录,以考校善恶,增损其算也。”如此说来,那六十年算总账的时间或是戊申之岁,故称为“戊申簿”乎?这也是猜测而已。这“戊申簿”很类似于官府的人事档案,要把生人的功过随时记录下来,再以此为据,增损人的寿命和禄位,其间分门别类,定有很多考究。
而陈叔文《回阳记》中的冥簿似比“戊申簿”更为丛杂,“凡行事动念,无不录者”,那就不仅限于言行,就是脑袋里想的,哪怕只是“私字一闪念”,也要记录在案。这本流水账“大善书黄字,小善书红字,大恶书绿字,小恶书黑字”,能让人看了“不觉毛骨悚然”,想必是狠狠地触及灵魂了。只是脑袋里转了个念头,就会被冥府侦知,这可能连潜伏在人身上的三尸神都难于做到了。但也不会是什么高科技,估计不过就是洋教中的告解、土教中的“交心”之类,变着法儿把你的心里话诓出来就是。可叹的是,一旦这种交心受到鼓励,成为风尚,摆起擂台,那就不止于深挖穷搜,甚至还要胡编乱造——当时或者以为是出了风头,成了交心模范,及至簿子一摊开,大算盘一响,便只有“毛骨悚然”了。
当然,如果动机好,真能淳化风俗,致君尧舜,手段的卑劣也不妨宽容些罢了,问题便在于,善恶簿可不是鼓励人学雷锋的。明人钱希言的《狯园》卷十一有“都城隍神”一则,正可看出正人君子们造善恶簿的用心。
明穆宗隆庆五年,北京一个十九岁的小秀才,聪慧异常,因与同学到西山游玩,遇一十六七的少女,二人眉目传情,正是张君瑞在普救寺撞着五百年前风流业冤的情景。小秀才回来后,难免就“求之不得,寤寐思服”,得了相思病。他的家教老师是个年轻的举人,也颇通人情事理,问出学生的心思,便要玉成此事,替学生写了篇祷词,二人便到都城隍庙去烧香祈愿。到此为止,实在看不出小秀才犯了什么错,谁知从庙里回来,都城隍爷就附体于巫师,对秀才发布了宣判:秀才命中应是万历二年的状元,享寿九十,其师也应是同榜进士。但如今减折其禄算,十九岁即夭;而其师则抽肠剐之。罪状是什么?是不通过“父母之命,媒妁之言”而企图和女孩子谈恋爱!果然,到第二天,小秀才梦见金甲神以斤斧凿顶,而其师则腹疼如绞,三日之后,双双毙命。至于那个山里的女孩子,想必也不会有好下场,因为按照“郿坞县”父母官的逻辑,小傅朋的“起淫心”都是孙玉姣“卖风流”的结果。
男女之情是最基本的人性,只是因为有此“邪念”,就连寿带禄剥夺干净,来个“斩立决”,其用心就是把人性彻底泯灭。看了这个故事,当时我只有一种想法:天地间无地狱则可,有则必为编这故事的人所设!这则故事到了清末,陈彝认为有助于世道人心,全文录入他的《伊园谈异》,而《谈异》一书又为谭复堂所称许,可见钱希言是不乏同调的。不要以为这些人真是不通“人道”的迂夫子,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,他们“遏塞本性的发露,却耽溺于变态的嗜欲”,越是那些满肚子猪狗杂碎的人,就越要装成正人君子;可是心中那一股邪念,却让他们无论如何也装不像,至多也就是一种没了人味儿的畸型怪物而已。陈彝在《谈异》中就曾慨叹人世官府不能把世人的一举一动一思一念都记录在案,认为冥府的善恶簿大可补阳世之不足。此人历官安徽巡抚、礼部侍郎,看来他是很想把阎王殿那套特务政治引进到官府中来治国治民的,其人格之卑、见识之陋可见一斑。清末小说《冷眼观》中有一位“每日同一班倚佛穿衣、赖佛吃饭的东西在一处鬼混”的陈六舟就是此公,小说中他最后死于吃了乩仙的灵药,怕也不是空穴来风吧。
宋元以后,冥府善恶簿基本上成了假道学中最低下那一档的表演道具。早在南宋时,这善恶簿就有另一种说法,即冥间有善、恶二簿,以人分别,即善人入善簿,恶人入恶簿。(见洪迈《夷坚志补》卷十六“太清宫试论”条。)至清人陆长春《香饮楼宾谈》卷下,又出现了“功过册”之说,即每人均立善恶之簿,除了“记生平禄业”之簿之外,还有一本专“记逐时功过”。某公自言于冥间看到本人的册子,就是儿童时取龟蛋为戏耍,不小心弄破,也要以杀生论过,而此公极为诚实,竟把自已一生最“无德”的事也做了公示:
回顾己身,胸前现墨字两行,大书“看淫书一遍,记大过十次”。
无独有偶,《聊斋志异》有“汤公”一条,是“道德家”的自述,也很像是假道学的“功过格”,在由生入死的瞬间,人一生的善恶都要像放录相带似的快进一遍,而这位汤公值得一记的最大“恶迹”竟然只是“七八岁时,曾探雀雏而毙之”。故事是他醒来之后自己编的,其人之虚伪矫饰历然如画。蒲老先生这篇文章如果不是意含讥讽,那就有些恶心了。
冥间的“功过册”就是人间“功过格”的翻版。道学先生们早请示、晚汇报,每天要拿出几个小时来斗私批修,再揪心撕肺地检讨批判一番,在今天看来,是很有些滑稽的,但在四十年前我们却力图把它普及成全民所有制,几乎达到“六亿神州尽道学”的境界了。
于是想到整整四十年前,我刚到农村做教员(说是初中,其实是“小学戴帽”),先参加一个教员学习班。一位老师发言,题目念出,令人骇异,是“狠批我的淫乱思想”。但听下去渐渐明白,他只是检查一件事,就是想把衣服上的布纽绊换成塑料钮扣而已。但他说“既有俊意,便有淫心”(“俊意”就是爱美的欲望吧?方音这句话念为“既有重意,便有硬兴”,虽然多次重复,还是听不懂,为此专门请教了发言者,所以才让我熟记至今),然后用当时的上纲上线法推演下去,起承转合,最后终于把自己推理成反革命坏分子(那时无论是什么犯,都要加上“反革命”三字的)。散会之后,我再见到这位发言者时颇为局促,盖怕这位“候补流氓犯”不好意思也。其实我真是多虑,因为此人不但绝无忸怩之态,而且很快便蒙领导安排为大会典型发言了。有人说,那最初的发言其实就是领导所策划。这倒也不必大加责难,因为当时的几十个讨论小组会都是面面相觑,冷清得实在让人难堪了。而大会之后的结果便是“激活”,再开小组会,每个发言者就都竞相“淫乱”起来了。
但如果以为我们小民那么容易就被修理成道学家的门徒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在那个禁欲的年代,人们的神经变得格外敏感,从刨白薯、打土坯到样板戏、讲用会,人们把双关联想运用得让中书君都要佩服。仅那个“淫”字就很能刺激想象(鄙同事說起时往往发出重音,一席话间,“硬”“硬”不止),从而不断地发挥、开掘,往往把一顿忆苦饭最后弄成八荤八素的大宴。先是有人低头吃吃窃笑,继而有人应和,于是渐渐把正题引入邪道,讨论便活泼起来,教育局的领导驾临到此,也只不过笑骂一句“操蛋鬼”以表示自己既不苟和也不禁止的立场,但心中也可能很是为自己的调控本领感到得意。在这时女同志往往有不必发言的特权,就是红着脸跑掉顺便溜走逛大街也没有人追究的。现在想起,四人帮一伙真是蠢蛋,蠢就蠢在真的以为普天下都让他们弄得舆论一律、思想一统,人人都成了机器人一号,岂不知人的天性和良知一样,都是不大容易被泯灭干净的。
于是继续发展,而更有一种冥簿叫“出恭看书之簿”,即凡有“三上”之癖者都要入册,大约是由专门在厕所蹲点的特务逐笔记下,最后阴司按其“厕筹”,夺其寿算。梁恭辰《北东园笔录初编》卷一“佘秋室学士”条云:
王取生死簿阅之,顾判官曰:“彼阳寿尚未终,何以勾至?”判官曰:“此人出恭看书,已夺其寿算矣。”王命取簿,则一册厚寸许,签书“出恭看书”四大字。[2]
看到此处,不禁骇然,我虽然只有一上之癖,却偏偏正是厕上!但窃思所以未提前被阎王接见之故,大约是因为如厕时从来不捧读圣贤之书,即是报纸也只看二手房广告的缘故吧。圣贤之书绝对不能入厕,这一点就是愚鲁小民也无须耳提即可明了。常见办公室同事惶惶然地在书堆中乱翻,那如果不是上级抽查,必是内急相催,此时你试着递上一本圣贤书,百分之百是要遭到峻拒的。而按诸葛恪鸡屎与鸡蛋“所出同耳”之例,那些只应在讲坛上宣示的心得肺得、高头讲章,自然也是不能入厕的。
不但古代,即是在我们“手不离红宝书”的年代,如厕时也遇到同类问题。曾见有一手高举另一手方便者,那动作虽然难度不大,却极难持久,绝非一般大众所能效仿,弄不好就一失手成千古恨。既然难乎为继,也就成了异类,而此人一入厕就高举,弄得正在方便之人忙手忙脚地紧跟,显然有诱人蹈入死地之嫌,于是便有人声而讨之,揭露此人意在让人把红宝书投于粪坑。好在他根红苗正,虽然其心叵测,但其情“朴素”,也就不了了之,可是这创举便也随之湮没。后来曾串联至南方一地,见街道上的公厕之外置一木桌,上铺红布,并有红纸提示,意谓供如厕者暂奉宝书于此。这设想的周到体贴极让人感动,可惜当时一些人不能稍忍忠爱之情,顺手牵走或以次换好的现象甚多,卒使善政未能“克终允德”,良可叹也。
但如厕总还是应该找些事来做的。古人言“贱人”四相,即“饭迟屙屎疾,睡易着衣难”,要想做贵人,至少也要在恭桶上消磨十几分钟才行。在那里无所事事是不合“禹惜寸阴”的古训的,所以你可以在那里“三省吾身”,也可以“养浩然之气”;及至渐渐做成贵人,自然就会明白,运筹帷幄,盘算着整人斗人,真是没有比恭桶之上更好的地方了。《汉书·汲黯传》中说,大将军卫青侍中,汉武帝“踞厕视之”,而对鲠直到不近人情的汲黯,只要自己衣冠略有不整都不肯接见。史家以此来证明武帝对汲黯的敬重,其实是大谬不然的。对曲学阿世的丞相公孙弘可以提着裤子出来接见,说明武帝对他的关系要比对汲黯亲近。而身为内朝领袖,卫青能荣膺为入厕之宾,一边翊赞猷谋,一边替万岁爷擦屁股,那才真正是“密勿大臣”的待遇。
有句话道是“为领导做一百件好事,不如与领导合伙干一件坏事”,不知这话是不是从汉朝那时传下来的,但明代肯定是已经有了。顾亭林曾引“时人之语”道:“媚其君者,将顺于朝廷之上,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时。”而更早一些,朱熹在宋孝宗时也曾上言:“士大夫之进见有时,而近习之从容无间。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,其议论又苦而难入;近习便辟侧媚之态,既足以蛊心志,其胥吏狡狯之术,又足以眩聪明,恐陛下未及施驾驭之策,而先已堕其数中矣。”说的正是同一道理。
而“燕退”之私当然也有层次之别。想必古代官场上自有一些“一般人就不告诉你”的秘诀,那向上进步的层次,在升堂、入室之后,倘若顶头的不是武则天而有上床之幸,那最高级的就只能是陪厕了吧。话扯得远了些,又未加考证,所以本人并不敢断言恭桶就是皇权政治中心的中心,但某些最高决策往往出于茅厕,却也是不能遽然否定的吧。
二〇〇八年八月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[1] 周大麻子的故事,在清末丁治棠《仕隐斋涉笔》卷一“一善免劫”条中则作王三麻子,大同小异,但更为生动详尽些。
[2] 《北东园笔录初编》所记是佘集对梁恭辰之父梁章钜亲口所说,云有广东吴某者来访,因延人,吴曰:“君其出恭看书耶?”佘怪之。吴曰:“我亦犯此罪过,去岁曾大病,梦入阴司,自念……母将无依,痛哭求阎王放还,待母天年。王取生死簿阅之,顾判官曰:‘彼阳寿尚未终,何以勾至?’判官曰:‘此人出恭看书,已夺其寿算矣。’王命取簿,则一册厚寸许,签书‘出恭看书’四大字。王展阅至予名,予方跪迎案前,叩头哀泣,因得偷目视册,果减寿二纪。予之上名即君也,君名下注‘浙江钱塘人,壬午举人,丙戌状元’,以下禄位注甚长,乃于‘状元’字用笔勾去,改‘进士’二字。”时佘闻吴言,方愕然痛悔,誓改前愆云云。佘学士亲口所言,不容你不信,而后来有朱海的《妄妄录》卷九“溺器上观书削禄”一条,更进一步坐实此事。山西神童刘戡,九岁即成秀才,可是到了中年仍是一领青衿,心中颇怪祖上必做了什么缺德之才,连累了自己的前程。至夜,其亡父现形,说:“你本当位列清华之选,只是因为大便时溺器上观书,亵渎了圣贤,故而削夺了福禄。杭州佘秋室才华命禄都远胜于你,尚且因此过丢了状元。你再怨尤,必增罪戾!”刘戡醒后不信,竟自带干粮来访佘秋室,问知果尝临溺观书,遂大哭而去云。
在线阅读网:http://www.yuedu88.com/